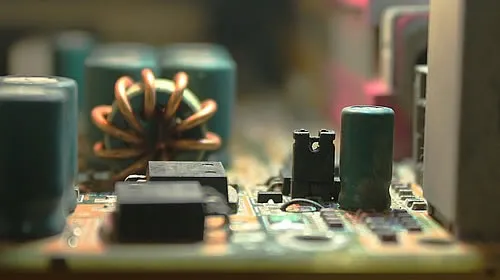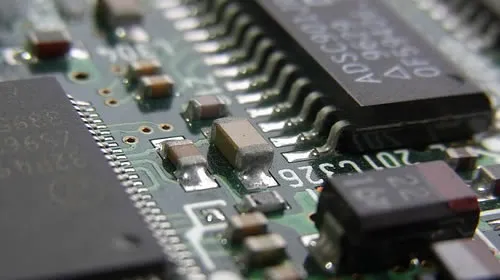百鸟等您到天明

作者简介 郑承军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教授,2010年哈佛大学东亚系高级研究学者,两本专著被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人生总是在没意义的日子里忙着有意义的事业,才让我们的人生在没意义的事务中凸显价值和意义。生存,貌似从黑夜到天明的轮回,其实,生存就是期盼。活着就是在无意义的打发时光中有意义地期盼天明。若无天明,何来盼头?文学家和哲学家都是以思考人生和审视存在为职业的,而电影人,是靠呈现这种思维与存在过活的,因此,电影人既需要呈现,更需要思索,成熟的电影人思索更甚于呈现,他们常常在生命和活法中苦苦思考、默默体味……电影是热闹的,但电影人是孤独的。在我年近半百的人生旅程中,也碰着个一些电影人,让生活和日子也些许充满电影的感觉和味道,时不时地在脑海里倒带、放映。其中,有一位,岁月的尘封差点让我遗忘了他的胶片,最近,一部因下跪排片引发争议的电影让我的大脑重新倒带,放映起与他相遇的日子……他的名字,叫吴天明。那是2010年10月,正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访学的我收到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的邀请函,邀请我到南卡罗莱纳州哥伦比亚城参加由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孔子学院主办,南卡大学影像研究所、哈佛大学“中国电影”项目、中国电影资料馆、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语言大学以及《中国电影市场》杂志协办的“1979年以来的中国电影在美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我从波士顿转了好几次飞机,一路困顿地到达这个南方小镇的时候,已是人仰马翻,在办理入住手续时,他出现了。他,就是吴天明。当时,他剃了个光头,穿着朴素的黑色夹克,透着敦厚、朴实、爽朗。刚见时,我的确有些惊喜,毕竟他是当代中国著名的电影导演和电影“教父”,拍摄了《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变脸》等影片,我都看过,着实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的优秀影片,堪称中国当代电影的教科书,他还提携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何平、周晓文、顾长卫等一批中国影坛响当当的人物,不由得让人心生仰慕。正在难堪不知道如何打招呼时,他先向我微笑致意。“这个地方中国人不多,你也是来开会的吧?”“是的,吴导,我从波士顿来。”“波士顿?东北部啊!不近啊!真是辛苦。我从加州过来的,也挺费劲,哈哈……”就这样,我们两个素不相识的华人在异国他乡的大学宾馆里相遇了,象两个老朋友一样开始聊天,搞得陪他过来的南卡罗莱纳大学的华人学者叶坦教授还误以为我们早就认识,说不用介绍了。这可能就是一种缘分,一种来自同胞同种的亲近。我知道他是受过苦、遭过难的人,但凡有些经历的成功人士,都不会把成功当作自己的标签,而更倾向于成为一个自然、朴实的普通人,吴导似乎就是这样的为人。在我的第一印象中,他不像一个叱咤影坛的风云人物,而更像一个早晨起来买豆浆、油条,爱聊天、爱遛弯的和蔼可亲的邻家大伯。接下来的开会的几天,我们一起参会、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一起散步,单一的“影坛大佬”的吴天明印象逐渐立体、丰满起来,他不是那种只谈电影的“专业狂”,而是一个热爱生活、向往自由、追求本真的汉子。那几天,南卡的天气特别好,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在南卡大学绿树成荫、花香鸟语的校园里,我们常常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看见花,他对我说:“你看那些遍地的野花,不是为了美丽而盛开,而是为了盛开而美丽。”看见树,他说:“这些大树好高,向下扎根大地,向上拥抱天空!”看见鸟,他说:“鸟是自由的,它用飞翔来表达自由。人要是会飞,该多自由。”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主动说起他与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的提携之恩,当我们聊到他们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他们很有才气,也很勤奋,机会当然会眷顾这些勤快的人。他倒是给我说,他到美国后,包过饺子、卖过面条、卖过速冻食品,还开过录像店,租带子为生。他说,美国的生活比起国外来,要简单清贫得多,但很实在。他很珍惜朋友的友情,说“多亏了有朋友,在美国才不孤单”。他实在,不爱显摆,就像校园里面那些小花、小鸟,真实、朴素、亲切,更像校园里的那些大树,正直、挺拔、大气。美国一别,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尽管他曾与我相约回国后去他北京亚运村的公司相聚,但由于各自繁忙,再也未曾谋面。这是人的常态,在杂事的混沌中我们经常就相互淡忘,再无交错。直到2014年3月的一天,他突然去世的噩耗传来,我才发现在我的人生际遇里还曾与这样一个慈祥可敬的老人同行过几天,那几天是那样的让人难以忘怀,开心、恬淡、舒适……吴天明走了,我再也不能按他所约在北京与他相见,美国的约定变成了永不能实现,心中真的涌上一股感伤和痛楚,在体内弥漫、游走、蔓延。肉身已去、灵魂不死,还是让电影史永远铭记有这样一个电影人曾经来过,虽然离去,但永不会离开。其实,联想起在美国吴导给我说过的他那些经历和故事,有时也想,可以慰藉吴导的是:天堂里再也没有“人生”“变脸”,可以安安心心地坐在一条平静流淌、没有航标的河边,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看人间岁月,熙熙攘攘,往日如烟。“水不洗水、尘不染尘,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吴天明走了,岁月依旧波澜不惊地打发着。说句实在话,在我的大脑容量里,吴导所占据的空间,正被纷繁复杂、杂多凌乱的事务、记忆、琐事慢慢挤占、甚至吞噬殆尽,直到一部电影的出现。 这部电影就是现在大火的《百鸟朝凤》。它所引发的讨论和争议,因吴天明而起,但已经远远超越了吴天明本身;因方励老师下跪祈求排片而起,但也似乎已超越了票房和情怀。可不可以这么说,中国艺术电影的宿命,不在情怀中爆发,就在票房中死去。《百鸟朝凤》从一部低成本的写实艺术片,似乎“鲤鱼跳龙门”,一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遗忘的历史事件,它所引发的对中国艺术电影的走向和命运的讨论,一定会成为中国电影历史中的一个坐标物,就像20年代电影《孤儿救祖记》在票房上的“孤儿救祖亦救市”,制片人的“一跪值千金”也使《百鸟朝凤》“乌鸡变凤凰”。但是,我想提醒人们的是,《百鸟朝凤》的“逆袭成功”,虽然要感谢方励的“跪”,但更要感谢吴天明的“拍”,没有吴天明的“拍得好”,哪有方励的“跪得下”。不能把关注点只放在电影的营销、炒作和噱头上,而遗忘了电影本身。《百鸟朝凤》是吴天明的遗作,也是吴天明的佳作。看过影片,我仿佛觉得主演不是陶泽如,而是吴天明。唢呐匠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像极了他在美国散步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我感觉,吴天明复活了。吴天明借一个唢呐匠的故事诉说了他作为一个电影人的人生追求、价值判断,以及社会高速发展、急遽变迁对命运冲击的无奈。唢呐就像他拍的传统电影,洋乐团就像商业气息浓郁的国外大片,在碰撞和冲突中上演着豁出生命、泣血坚守的执着和坚定不移。听说当年他看了肖江虹的中篇小说《百鸟朝凤》后,立刻就联系肖,希望将它拍成电影。他说“之所以对《百鸟朝凤》感兴趣,是因为作品中有一种气质符合我的电影创作风格,特别是在今天,人物的真善美已经不被许多艺术门类的创作者所关注,作为作家和电影导演,对此都应该有所担当。”真善美,就是吴天明矢志不渝、泣血坚守的道德操守和价值担当。吴天明的“真”体现在他看重真情实意,不喜欢虚头巴脑。在《百鸟朝凤》“收徒”的桥段中,焦三爷本来是不想收天鸣的,但当天鸣扶起不慎摔倒的天鸣爹时,流下的眼泪打动了焦三,他看到了孩子的真心和真情。在“选接班人”的情节中,焦三爷选中了老实厚道、踏实肯干、真心实意的天鸣,而没有选择天赋更高、更加机灵乖巧的蓝玉,是因为在吴天明的价值观里,道德品性是第一位的,天资、技巧退到了第二位。两个孩子都很优秀,但天鸣更加真诚、更加守拙、更加懂得坚守。焦三没有看走眼,当天鸣出第一次活挣钱回来,就带着烟叶、花布、鲜肉来看师父和师娘,并和师父美美地喝了一顿,焦三说:“不要只盯着手里的钱,要盯着手里的唢呐。”“真正的唢呐是吹给自己听的。”像极了吴天明的性情中人的性格。天鸣早晨离开家看见师父师母在地里劳作,便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师父和师母,以表他尊敬师长、师恩难忘的真心实意;当商业大潮席卷农村,唢呐不再成为仪式上的必需,唢呐匠们纷纷外出打工,只有天鸣还在坚守,宁肯不娶媳妇,宁肯不到外面打工挣钱,也要把游家班维持下去。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为了生计,师兄师弟们纷纷外出,班子再也组不成了,连最后在师父坟前吹“百鸟朝凤”,也只有天鸣一个,他穿戴整齐、情真意切地在坟前仰天吹奏,流露出一个真汉子的真性情。吴天明的“善”体现在他总是为人着想。在美国开会那几天,他总是从会议主办方的立场考虑,不提给别人添麻烦的要求。他是一个十分惜才的人,敢于提拔张艺谋等人,就表现了他珍惜人才,总是从青年人渴望成才的角度想问题,帮他们排忧解难,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成才环境。在《百鸟朝凤》中,焦三爷对徒弟要求十分严格,甚至到了严苛的程度,但关键时刻,他却总是关爱徒弟。天鸣在河边练“吸水”,突遇大雨,师父师母赶到河边,师父一把抢过唢呐,把雨衣给天鸣披上,还把头上自己戴的斗笠摘下,让天鸣戴上。当天鸣身体不适,吹不了“百鸟朝凤”时,已经病重的师父主动顶替,结果把肺血都吹出来了……吴天明的“美”体现在他有一颗公正之心和大美情怀。《百鸟朝凤》中,一家品性不端的村干部家出高价请焦三爷吹“百鸟朝凤”,但焦三爷认为他配不上,坚决不吹;而当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村长过世时,焦三爷不顾身体已经病入膏肓,泣血吹奏,终因体力不支倒下,还叮嘱天鸣接着吹下去,展现了焦三爷不畏权贵、刚直不阿、公正侠义之“美”。而在河边学鸟叫的桥段中,风吹芦苇、鸟语花香,焦三爷与徒弟们竖起耳朵、潜心模仿,将一幅师徒学艺、师徒情深的场景刻画得淋漓尽致,怎一个“美”字了得!《百鸟朝凤》的结局是悲壮的,人们还是无法撼动市场经济的冲击,都外出打工了,吹唢呐的人少了,游家班也只剩天鸣一个了。吴天明的结局似乎也是悲壮,收山遗作差点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只能靠“下跪”的苦情来感召观众,让流连在《美国队长3》旁边的观众从刺激炫目的声光电闪中回过神来:哦,差点忘了,这儿还有一个老老实实叙述故事、土得掉渣、平淡无奇的吴天明电影。哈佛大学著名教授亨廷顿说:“在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中,核心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在文明的冲突中,问题的核心却是‘你是什么’”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个论断的正确与谬误,但“我是谁”“我要干什么”却真的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应该好好思索。我认识的吴天明,一直在思索他是谁,他想干什么,而且,矢志不渝。在水泥森林的喧嚣都市,听的最多的是轰鸣的马达声和刺耳的汽笛声,悠扬婉转的鸟鸣和叽叽喳喳的鸟噪已成奢侈品。吴天明想,他是一个电影导演,他想给观众在物欲横流、烦躁不安的时代呈现一曲鸟语花香的田园牧歌。世界是喧闹的,但心应该静下来。《百鸟朝凤》中说,只有品德高尚的人在葬礼上才能享用“百鸟朝凤”的唢呐吹奏,吴天明在不经意中用《百鸟朝凤》为自己的生命盖棺定论,这不是他的本意,这是天意。在美国时,他说他喜欢欢悦的小鸟,在电影里,他用河边的百鸟争鸣来幻化世界的多样和丰富。百鸟朝凤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是,让欢快的小鸟永远萦绕在自己的生活,倒是每个快意人生的人都可以做到。天明,您可能并不期冀百鸟朝凤,但我敢肯定,因为您的厚道、朴实、亲切、执着、思考,百鸟都会喜欢您,一定会等您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