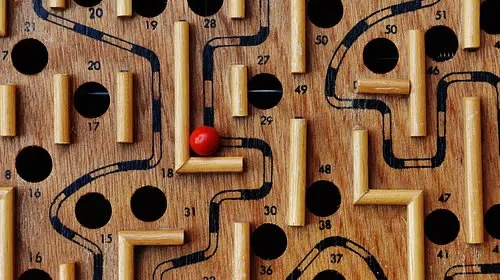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的意思是什么 蒌蒿满地芦芽短的读音

意思是:河滩上已经长满蒌蒿,芦笋也长出了嫩芽,正是河豚要逆流而上的时候,从大海回游到江河里来了。
全文如下: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两两归鸿欲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
翘翘错薪,言刈(yì)其蒌(lóu)。之子于归,言秣(mò)其驹。
——那片茂盛的蒌蒿,砍回来当柴;在你出嫁之前,给你喂好马。
元旦刚过,北京的早市里,蒌蒿已经上市,十块钱一小捆。闻了一下,并不太香,应该是还没到季节,或者是大棚里培育出来的品种,味道不如家乡过年时吃的那样纯正。在江城,正月间气温依然很低,在交通还没有那么方便的年代,菜场里的蔬菜不会很多,菜园里也只有大蒜叶、红菜台和白菜苔之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蒌蒿的嫩芽,江城方言称泥蒿,这种生于江河湖泽的野菜,开始出现在菜市场,一跃而成为餐桌上的新宠,无论清炒还是炒腊肉,都有一种异香,那是蒿属植物特有的味道。
↑常见的清炒蒌蒿
1 蒌蒿与结亲
蒌蒿(Artemisia selengensis),菊科,蒿属,广泛分布于全国各省区,北方更常见。蒌蒿是多年生本草植物,三国时吴国学者陆玑就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做了详细的介绍:
蒌,蒌蒿也。其叶似艾,白色,长数寸,高丈馀。好生水边及泽中,正月根牙生,旁茎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叶又可蒸为茹。
原来早在三国时,人们就开始在正月间食用蒌蒿的嫩茎了,只不过那时候是生吃,并非我们今日的清炒或者炒腊肉。
↑蒌蒿叶片细,边缘有锯齿,叶片背面白色;主要的食用部分是蒌蒿细嫩的幼茎,而不是叶片。
但在更早以前的《诗经》时代,“蒌”并非作为食物,而是柴薪。《诗经·周南·汉广》: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
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毛传》对“蒌”的注释为“草中之翘翘然。”《汉广》中这句诗的意思是:那片茂盛的蒌蒿,砍回来当柴;在你出嫁之前,给你喂好马。后来诗人海子那句“喂马、劈柴、环游世界”估计也从这里来。
《汉广》这首诗说的是男孩追求心爱的姑娘而不得:“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所以诗中写的砍柴作炬,喂马迎亲,只能是充满哀愁的想象。根据魏源《诗古微》统计,《诗经》中除了《汉广》,另有四首诗都以砍柴起兴娶妻,所以嫁娶之日,燎炬为烛,大概是那个年代的传统:
三百篇言取妻者,皆以析薪取兴。盖古者嫁娶,必以燎炬为烛。[1]
而蒌蒿的确是一种易得且易燃的柴薪。[2]儿时在乡间,山野秋来,百草枯黄,家人去田埂去小山上砍柴,其中多杂有蒌蒿。干枯的蒌蒿清香依旧,那是秋日黄昏的味道。
↑诗经中的蒌蒿
2 蒌蒿与河豚
最晚在东汉,人们就发现蒌蒿不仅可以做柴,还可以用来吃,而且那时还有一种比较高级的吃法——炖鱼。
东汉许慎(约58~149)《说文》:“艸也,可以亨魚。”[1] 对于“艸”这一字,晋郭璞(276—324)注《尔雅》时说:“蔏蒌,蒌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东用羹鱼。”[2]“初出”时的蒌蒿,即蒌蒿的嫩茎。
《说文》中对“蒌”的解释就一句话,“可以亨魚”乃是作为“蒌”之为“蒌”的重要信息。可见,蒌蒿与鱼同煮的吃法,在东汉,尤其在江东一带,已经特别流行,但究竟炖的什么鱼,尚不可知。不过这种吃法一直延续到宋代,到了宋代,人们拿蒌蒿炖的鱼,乃是大名鼎鼎、毒性与美味并存的河豚。我们不妨先从苏轼那首广为传颂的诗说起: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篓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元丰八年(1085),河南汴京,苏轼(1037—1101)为僧人惠崇(965-1017)的画题诗,这是其中一首。惠崇的画作已荡然无存,但苏轼这首《惠崇春江晚景》却流传至今。[5]诗的前三句写实,二十一个字中涵盖了绿竹、桃花、江水、鸭、蒌蒿、芦芽共六种江南春季风物;后一句联想,此时正是河豚逆流而上,入江产卵的季节。
河豚是硬骨鱼纲、鲀科鱼类河鲀的俗称,因捕获出水时发出类似猪的叫声而得名为“豚”。 河豚平时生活在暖温带及热带近海底层,每年3月游至江河,进入长江的河豚,一般于4~6月在中游江段或洞庭湖、鄱阳湖中产卵。苏轼此诗最后一句的联想有其实际依据。
河豚味道鲜美,但毒性不小,处理不当会因此丧命。《山海经·北山经》载:“其中多䰽䰽,食之杀人。”[6]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不过宋代人似乎已经掌握吃河豚而不中毒的方法。
↑对河豚有兴趣的,可以参阅这篇 文章
北宋景祐五年(1038),梅尧臣(1002-1060)在建德(今安徽省东至县)任县令五年期满,时范仲淹任饶州(今鄱阳)知州,二人同游庐山,席上有人谈论河豚,梅尧臣很感兴趣,作《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以记之:
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
其状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犹吴蛙。
庖煎苟失所,入喉为镆铘。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
持问南方人,党护复矜夸。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
……
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
梅尧臣问南方人,既然河豚有毒,何必冒着生命危险去吃它?但众人都说河豚味道鲜美无比,似乎根本没有中毒这回事。可见宋代人在食用河豚方面已经很有经验了。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评论此诗时有言:“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7]关于江南食河豚,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lěi)(1054~1114)在历史琐闻类笔记《明道杂志》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河豚鱼,水族之奇味也,而世传以为有毒,能杀人。中毒则觉胀,亟取不洁食乃可解,不尔必死。余时守丹阳及宣城,见土人户食之,其烹煮亦无法,但用蒌蒿、荻笋、菘菜三物,云最相宜。用菘以渗其膏耳,而未尝见死者。……此鱼出时必成群,一网取数十。初出时,虽其乡亦甚贵,在仲春间,吴人此时会客,无此鱼则非盛会。其美尤宜再温,吴人多晨烹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温以进。
由此可见,北宋时期的苏吴一带,河豚乃是非常名贵的食材,仲春时节,吴人宴请,如果没有河豚,都算不上盛会。而烹饪河豚的方法,却是以菘菜、蒌蒿、荻芽三物同煮,仿佛此三者能解毒一般。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亦有相似的记载:
严有翼《艺苑雌黄》云∶河鲀,水族之奇味,世传其杀人,余守丹阳、宣城,见土人户户食之。但用菘菜、蒌蒿、荻芽三物煮之,亦未见死者。[8]
菘菜可能是我们今天常见的十字花科、芸苔属的小白菜。荻是禾本科、荻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荻芽即其嫩芽,类似小笋,可直接食用,用来做菜或罐头。[9]“篓蒿满地芦芽短”中的“芦芽”,或许就是荻笋或荻芽,所以这句诗写的其实是一道菜啊,可别忘了,苏东坡的另一个身份是美食家。
↑中式红烧河豚
南宋绍兴间(1137-1162年)进士林洪写有一本烹饪著作《山家清供》,以素食为主,共记104道菜品,其中就有“蒿蒌菜、蒿鱼羹”:
旧客江西林山房书院,春时多食此菜。嫩茎去叶,汤焯,用油、盐、苦酒沃之为茹;或加以肉,燥香脆,良可爱。后归京师,春辄思之。[10]
《山家清供》的书名取自杜甫诗“山家蒸栗暖,野饭射麋新。”书中所记菜品以素食为主,多为山居待客所用的清淡饮馔。蒌蒿作为山野时蔬,自然也入选在列。有趣的是,林洪这段关于蒌蒿做法的记载——或汤焯,或加肉,已与今日之吃法相去不远。当年林洪客居江西,年年春天都能吃到蒌蒿,后来回到京师没得吃了,到了春天就会想念这道菜。多么真实、可爱的记录?
蒌蒿之美,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