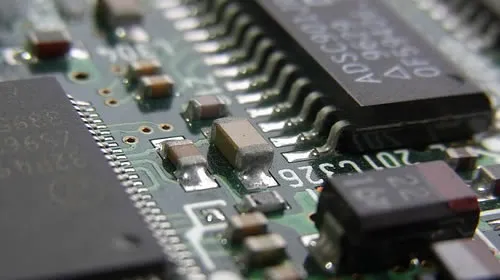厦门记忆:从“浮屿”讲起

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如果您满意于下面的图文,请让更多的人关注“鹭客社”。
一.浮屿汉语中的“屿”字,闽南话读“su”,鼓浪屿读“go-long-su”。厦门市区的厦禾路与思明北路交汇的地方,有几座三、四层的商住两用楼宇,被当地人称为“浮屿”,闽南语读成“pu-su”。明明是个繁华市区,却被称作“岛屿”。查考地方志,有两种解释:一是说这里本来就是个小岛,后来厦门市区扩建,填海筑路,浮屿与市区相连了,百姓口中仍保存旧日称呼“浮屿”;第二种说法是,站在厦禾路上,往北看,思明北路分成两叉,中间夹着的那座建筑,像是一个浮在水面上的岛屿。1961年,我从新疆来厦门投亲,有时会住在浮屿的姑妈家。姑父袁迪赉(lai)医生,解放前在浮屿一带行医,买下思明北路140号,楼下作诊所,二楼住人。姑妈家隔壁,是厦门市图书馆,文革期间改为少儿图书馆。表姐有一张借书证,每次可以借14本书。我从《十万个为什么》看起,到《红旗飘飘》、《小城春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得课业荒废,差点小学毕不了业。姑妈家的街对面,是著名的开明戏院。戏院沿街一层是售票大厅,二楼是舞台,正对着我家窗户,一家人天天都可以免费看戏。在那个饥荒年代,厦门的戏迷热情不减,夜夜笙歌、锣鼓喧天。戏院每天上演高甲戏、芗剧,有时还看到几位演员在台上斯文地弹唱一种叫“南音”的曲艺节目。多年以后,我在台湾观摩歌仔戏,其音韵、表演,令我忆及儿时享受开明戏院演出的美好时光。开明戏院隔壁,是思明区防保院,一个由许多个体医院、诊所合并而成的社区医院。我姑妈是该院的助产士,几十年来为浮屿一带居民接生,不可胜数。在附近的第四菜场,凡有称呼她“先生娘”(厦门人对医生太太的尊称)的菜贩,都是不会向她收钱的。思明北路与厦禾路交界的街角,有一间食品商店,是我经常驻足停留的地方。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食品都是配给供应的。厦门市民每月可领到一种可以买点心的票证,叫中级饼票。姑妈还是心疼娘家人,每个月总会背着她的儿女们,偷偷塞给我一张中级饼票。我攥着这份姑妈的心意,在那家店的柜台前徘徊、纠结:到底是买一块杏仁酥?还是蔴糬?就像哈姆雷特反复叨念: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厦门岛被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装点得更加美丽,更加引人注目。希望那些记载着这个城市发展经历的老地名,没有被遗忘。后排左一是作者二.地瓜腔我出生在漳州,一岁时被父母带去北方生活,直到十岁时,才回到厦门读小学。我寄住在姑妈家,众表兄妹和邻居们讲的厦门方言,即闽南话,我是完全听不懂。不会讲厦门话的我,搭公共汽车、买东西都不敢开口,生怕被别人认出是“北贡”。然而,我的“自卑感”在学校里,又成了自豪。那几年,厦门大力推广普通话,我的语文老师孙允贞,就说的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同学们没有几个人,能用普通话把“二”读正确,大家互相调侃自己的“湖建话”是“地瓜腔”。后来,我离开了厦门。每每在广播电视节目里听到闽南话,成了我思念厦门的纽带。八十年代,在学校的中秋晚会上,我的一曲闽南歌《天乌乌》获奖(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写成“天黑黑”)。可能是我报名时用的是“台湾民谣”,符合当时统战的意味,才被领导赏识的吧。现在的年轻人,个个普通话说得倍儿棒,都不喜欢说自己的家乡方言,地瓜腔都快要失传了。《潜伏》里扮演翠平的演员,是泉州出生的?我还有点不相信。去年,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厦门,正逢星期天。我到人称“中华第一圣堂”的新街礼拜堂,参加主日崇拜。我与全体会众起立齐唱,《闽南圣诗》中的一首《天父爱我歌》。咦?我怎么听得是:(天爸疼我)?仔细思量,闽南话中,将上帝的爱,比喻作父母对儿女痛惜、爱怜的意境表达,真是很准确、传神。礼拜结束了,邻座的一位慈祥老者跟我打招呼:“先生您是从外地来的吧?听闽南话有困难”?“哦,不、不,我听得懂,我是漳州出生的,只是离家太久了”。“是的,厦门话融合了漳州、泉州等闽南地区的方言,是一种很好听的语言,她保留了很多中国古代的文字和发音。欢迎您回到厦门来”。我目送这位可敬的老人,缓缓走出礼拜堂。旁边的人提醒我:“他是天天在电视上教厦门话的周教授,可有名啦,你都不跟他照张像”?新世界大楼三.厦门第一高楼在厦禾路与故宫路交汇处,有一座六七层高楼。知道它的人都会说:哦,那是厦门感光厂。而年长的厦门人,都称呼它:新世界。这座在当时的厦门第一高楼,是房地产开发商汪昌庆,仿照上海的大世界游乐场,于1932年建成的,取名新世界游乐场。新世界内设京戏、闽班、台湾戏、有声电影等表演节目,和其他娱乐设施。日寇占领厦门期间,市面百业凋零,新世界只能关门歇业。据老人说,新世界大楼住过日军的伤兵。这是可能的,有人曾经在那个院子里的防空洞里,捡到过子弹壳。1946年,福建省立医院的一部分,从南平迁来厦门,使用了这座厦门人喜爱的大楼,并改名为厦门第一医院。第一医院的旁边,是一块荒地。一群有为的知识分子,在政府的支持下,办起一所“厦门私立文化学校”,这就是日后的厦门市第六中学。1949年,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部林梦飞将军,识时务地起义了,保住了身家性命和家产。林与他的多年好友张圣才,合伙办起了厦门感光化学厂,生产飞天女牌的胶卷和相纸。初期,厂房设在厦鼓轮渡码头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厦门开始大办工业,市委书记袁改,把他的爱将谢崇永派来感光厂加强领导,并将工厂迁往厦禾路的新世界大楼。厦门第一医院获得更多发展,搬往镇海路现在的地址。厦门市第一任市长梁灵光,调任中央轻工部领导。他继续关心、支持厦门感光厂的成长、发展。飞天女牌的感光材料,是享誉全国的名优产品。堪称厦禾路新世界大楼里飞出的“金凤凰”。四.番薯签饭1963年,我和一群从“三年大饥荒”中成长的孩子,考进了福建省重点中学:厦门一中。漂亮的校舍、宽阔的体育场、令人敬畏的王校长和老师们。校门口的竹寮,是我们学生的饭堂。校园坐落在厦门深田路的尽头,当年就算是城市边缘了。家住市内各处的师生们,午餐都得在学校解决。每天上课前,大家把自己带的米装进瓦罐(饭钵子),按比例加水,然后放在食堂的大蒸笼里。我用的是舅舅从上海买回来的铝饭盒,颇有点与众不同。午餐时间到了,大家纷纷在大木架上找到自己的饭钵,再买一份饭堂提供的菜。素菜通常是:清炒空心菜或瓠子,五分钱。荤菜是:一勺红烧肉,或两块煎带鱼,一角钱。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馋呵,我只能一天荤,另一天用家里带的菜脯和酱瓜仔配饭。这天,我被老师留堂训话,等我到了学生食堂,只有我的铝饭盒孤零零地在架子上。匆匆打开一看,不是我的!一定是哪个冒失鬼拿错了饭盒。这是一盒一半番薯签(就是地瓜干)一半米混合的饭。我们的国家在粮食紧张的年代,用高产的地瓜,代替城市人的口粮供应。地瓜切成丝、晒干,大概是五斤抵一斤米。第二天,我寻到了自己的饭盒。里面依然是番薯签和米各半,只是有一块咸鱼干。温馨的“冒失鬼”,用这样来表示歉意。不知当年的同学们,现在还好吗?请与我联系!悠悠岁月,我们都成了爷爷奶奶了,并且都犯同样的错误:把自家的孙儿,统统养成了肥仔、胖妹。这也许就是我们童年时代,饥饿的心理阴影还没有消失的缘故。上学的时候,我最反感忆苦思甜大会了,老贫农在台上声泪俱下,我在下面看功课。咦,怎么今天我也忆苦思甜了呢?看来,我真的是老了。作者简介:陈宣明,厦门人,海外华人LOOKERS鹭客社 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欢迎关注鹭客社,投稿联系微信号:DONGE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