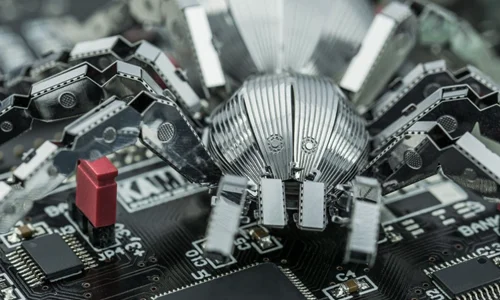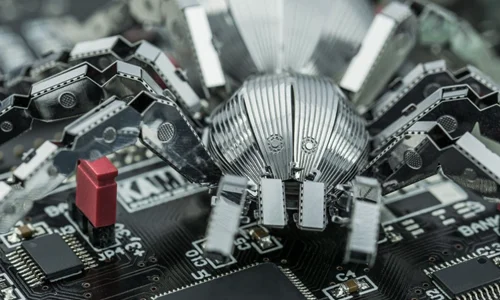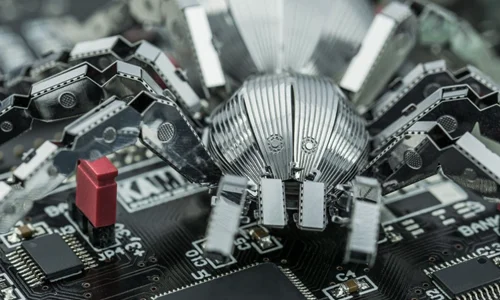
阿富汗妇女的遭遇前所未有的占据各大媒体头条。在国内,引起的关注热度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通常国际关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通常以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大国关系作为常用词汇。妇女虽然占世界人口一半,但似乎与国际关系不沾边。更不用说妇女因为受到男性歧视而得到全世界的关注了。这次人们关注塔利班以极坏的方式对待妇女,这个现象当然说明妇女权益受到的关注多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得是多坏的对待才能引起这般同仇敌忾。所以,此事即使称不上反常,也算得上罕见,值得写几个字。一 塔利班十宗罪我们先从塔利班的十宗罪说起。女性必须穿着“布卡”,即从头蒙到脚,只在眼睛部位采用网纱。“布卡”的作用就是将女性非人化,就是令她们看起来不像个人,没有人形。布卡十分厚重,空气流动不畅,会导致呼吸困难。眼睛处的纱窗,会大大局限女性的视野,过街变得危险。如果不小心露出脚踝也会被毒打。在市场上买东西时,不得露出手来。小女孩从8岁起就被要求穿上布卡。布卡不仅是一种囚服,还是精神上的羞辱。穷困人家买不起布卡,必须等邻居家的有空时借一件才能出门。残疾人等有特殊需求的,就更无法出门。因为布卡要么使她们无法行动,或者罩不住辅助设备,比如轮椅。⊥1413⊥岁以上女孩不许上学。偶尔会容许在家里教育女孩子,但多数时候是镇压。女性不许进入社会工作。塔利班1996年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关闭喀布尔大学。这几天他们正在将女性从银行、医院、学校等工作岗位上赶回“家”去。没有男性亲戚陪同,妇女不得出门。如被发现,将被在大庭广众之下鞭打100下。医院里,男医生只能隔着罩袍对女病人进行检查,导致无法进行正常的诊疗。塔利班治下女性健康状况恶化,生育死亡率是世界第二高:每100位妇女中有16位死于生孩子。小孩也是如此。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每1000个小孩中就有165个活不到一岁。要求涂黑窗户,防止有人从外面看到屋内的女人。将女性关进暗无天日的屋子里,变成事实上的囚徒。这给女性心理健康也带来极大伤害。阿富汗女性抑郁和自杀的比例很高。女性会吞服电池酸液或者清洁剂自杀,就像中国农村妇女喝农药自杀一样,因为这些物品是她们能够够到手的东西。妇女不能乘坐出租车,只能使用专用公共交通工具,这些车子的车窗拉着厚重的窗帘,以便不被街上的人看见。“通奸”有罪。这里的“通奸”甚至包括只是跟一个非男性亲戚走在一起。就会被用乱石砸死的办法处决。娱乐有罪。塔利班将女性囚禁在“家庭”里,如果她们生活的地方还能够被称为家庭的话。孩子们不许唱歌,不许放风筝。一个7岁的小女孩会因为穿了白鞋子而受到毒打。以婚姻的名义强奸女性。在有些地区,塔利班分子破门而入有年轻女性的家庭,宣称要与该家庭里的年轻女性“结婚”,几天之后,他们宣布“离婚”,然后离开。有时候,一位女性被迫持续不断地进入这类“婚姻”当中。这是他们为发泄自己的性欲,将其奴役行为合理化的方式。他们玩弄女性,还要将这种行为美化为“婚姻”。同时为了逃避婚姻的义务,又单方面宣布结婚和离婚。说白了,就是,“我要强奸你,以婚姻之名”。二 塔利班极致罪行的心理根源塔利班对待女性的穷凶极恶,不能用常理解释。他们得的是一种病,一种在人类男性中广泛存在的病。这个病叫做“厌女症”,详细病理分析可见上野千鹤子教授的《厌女》那本书。在这个病上,塔利班病入膏肓。塔利班极度野蛮的另一面,是他们的极度虚弱。第一,他们担心女性受过教育以后,她们会在学校或者社会上与男性竞争。第二,他们认为女性露出脸庞容易“腐蚀”男性,让他们变得不“纯洁”。这种看法隐含的前提假定是:男性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性欲。在管理自己的性欲上,男人是脆弱的、无能的、是无力的。他们假定只要一个男的看到一位露着面容的女性,就会瞬间难以控制自己的性欲。我们知道,动物们一般有固定的发情季,人类理论上可以随时发情,但在日常生活中,男性发情仍然需要很多外在和内在条件。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男性仍有自己的社会规范。但是在塔利班的教义假设中,这些都不存在。第三,他们假定男性的天职是捕猎别的男性的女人。他们把女人看作猎物。在猎人眼里,别的男性就像天上捕猎的老鹰一样,随时可能来掠夺自己嘴中的食物,所以必须把这个食物打扮得丑陋,让捕猎者失去兴趣。这是一种彻底物化女性的观念。第四,他们还对自己非常没有信心。他们假定女性十分淫荡。只要女性看到别的男的,就会离他而去。所以他们要将女性禁锢在屋子里,不能让别的男人看到。所以,在塔利班的脑子里,世界是一个大猎场。男人之间相互抢夺女性。他们需要看紧自己的女人,防止别的男人觊觎自己的财产。在他们眼里,女性不是生活的伴侣,不是寻求美好感情的对象,而仅仅是猎物,是财产,是性奴。他们不能理解人类正常的情感。抢夺猎物,满足性欲,繁殖后代,就是塔利班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这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世界观。塔利班男性跟女性的关系,与情感无关,与征服有关,与占有有关。在对待女性问题上,甚至不应该将他们比作禽兽。因为我们在禽兽的世界里也看不到这种残暴。禽兽的世界没有同类相食,没有虐待,没有性虐待,没有羞辱,没有剥削。这个,叫做男性的“厌女症”。 三 不仇恨妇女就不成其为塔利班在传统的普什图地区,女性一直过着被严格限制的生活。普什图价值(Pushtunwali)认为女性的美德是家族与部落荣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塔利班得势之前,如1994年的坎大哈城,1996年的喀布尔和1998年后的大部分北方地区,阿富汗妇女长期被认为是低男人一等,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法律上。在沙里亚法治下,女儿享有的继承权是儿子的一半,女性在法庭上的证词的效力是男性证词效力的一半。女性在生育计划和性权利上也受到很大限制。虽然这个时候妇女地位不高,但与其它传统社会相比,还在可以理解的范围。但在塔利班这股极端群体中,女性价值和地位被极端践踏。塔利班将女性视作事关“男性荣誉”的事务,彻底将女性物品化、非人化、性资源化。这与塔利班的滋生土壤有关系。塔利班是在从阿富汗内战中逃离的人群聚居的难民营中成长起来的。世界上有几千万难民,她们/他们逃离家乡,在其它国家勉强有一席存身之地。因为是不被所在国接纳的边缘人群,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在这种生活中,极端宗教主义找到了它的信徒。由于处于弱势地位,由于那种失家离国的悲怆感,这些圣战士们对待女性就特别恶劣。正如杨笠最近所说的,不能跟男人开玩笑。因为男性的心灵过于脆弱,你只能调侃男性的成功。当男性认为自己是失败者之时,因为无法正视这一失败,他们往往恼羞成怒,将怨气撒向比他更弱势的人。信奉极端主义的塔利班圣战士们再次逼迫女性戴上面纱,不许她们自由行动。最关键的是,如何对待女性,成为他们展示自己与苏联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权不同的重要象征。也是他们认为的与腐朽堕落的西方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如何对待女性,决定了他们之所以为他们。如果他们像其它人群一样对待女性,他们就不是他们了。所以,塔利班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把女性当奴隶的男人。美国战争学院的中东问题专家Larry P. Goodson教授的研究发现塔利班因为只能作为一个军事团体活动,所以他们唯一可以辨识的社会政策就是对待女性的政策。塔利班几乎没有行政人员,他们没什么钱,经济来源单一,亦即他们没有更多的政策需要制定。不要说现代政府了,就连传统社会中需要处理的一些社会政策,如医疗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等,塔利班都不需要去面对。所以它的关注点就是规制女性。它最有效的治理部门是“促进美德和惩治邪恶部”。塔利班掌权后,无论在多大地盘上,第一件事都是规制女性和“纯洁”社会。他们沿街巡逻,紧盯人们的穿着、有没有蓄胡子、打游戏、娱乐、跟外国人接触,特别是女性的外貌和行为。总结一下,塔利班仇恨女性是出于以下几点原因:疯狂厌女的意识形态。战斗之外,塔利班没有别的政策,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规制妇女上。维护塔利班队伍团结。最基层的塔利班分子来自极端贫困家庭的青少年,没有接触过外部世界。塔利班上层通过向他们灌输仇恨女性的“纯洁”思想来凝聚他们。而塔利班分子之间的情谊和认同感,也需要通过对女性的仇恨来凝聚。中国男性前些年间流传的“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的战斗情谊,就是一个男性之间通过共同的对女性态度来结成伙计、结成战斗团体的例子。仇恨女性是塔利班分子的“投名状”。总而概之,塔利班唯一的政策就是培植他们的伊斯兰主义身份。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反女性还与反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女性的自由是西方的腐败产物。他们反对现代化与他们仇恨女性是一体的。他们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反对世俗化,他们也反对自由。可以说,在塔利班的社会中,女性根本就不是人。许多人理性论证说,塔利班这么做,损失了一半人口的资源,无法利用女性的才智来建设社会,太可惜了。这完全是对牛弹琴。在塔利班的思想中,女性要么供男性发泄性欲,要么是能够为他们繁殖后代的工具而已。所以塔利班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非理性的东西。他们是理性的,只是他们的理性是压迫妇女。在所有现有的文化中,可能除了北欧少数几国,都存在着仇恨女性的根基,只是程度不同。当然,程度不同也是有意义的。美国支持特朗普的相当一批人就是仇女者,他们对于女性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取得的进展充满仇恨,觉得自己的东西被女性抢走了:工作机会、金钱、社会地位、学识等。它伤害性相对较小的表现形式就是前些年中国社会嘲笑女博士为“第三种人”。男性因为嫉妒女性,他们会妖魔化女性、污名化女性。到了塔利班这里就是将这种仇恨推到极致。这种嫉妒和仇恨的假设前提是,此类男性觉得自己比女性优越,自己应该得到比女性更多,如:权力、地位、金钱和性。简而言之,就是他们是优等性别,女性是次等性别。他们为女性在保护自己权益方面取得的进展而愤怒。他们想要的就是压迫女性。阿富汗不是没有过解放妇女的现代化改革,但塔利班两次取胜,他们代表的暴力和对女性的压迫,说明女性解放面临的反对势力是多么顽固。塔利班再度执政,为全球女性敲响了警钟:来自男性的仇恨和压迫不会轻易走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