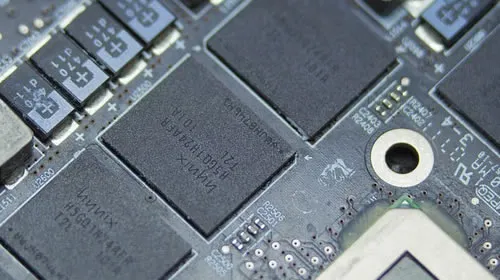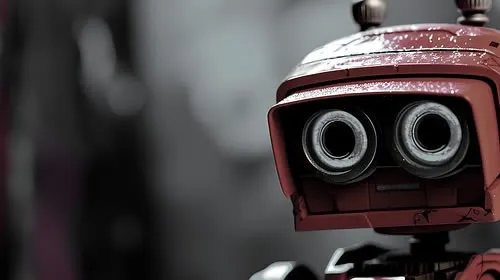法斯宾德75周年诞辰:嗑药、酗酒,创造德国新电影

喜马拉雅/爱发电APP关注深焦Radio苹果播客/小宇宙订阅深焦DeepFocus Radio 心碎之家:法斯宾德的德意志三部曲The Criterion CollectionHeartbreak House:Fassbinder’s BRD Trilogy文/ 肯特·琼斯译/ 莫妮卡编/ 白鸥2003年9月30日世人都说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死于毒品,但再三审视他的作品后,我对此持不同的观点。他曾讲过一句人尽皆知的话,大意是他正努力用自己的电影作品造一间房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数电影人都未能完成他们的房子,留得半壁空屋。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和约翰·福特(John Ford)等是极少数例外,除此之外,法斯宾德是唯一留下一间美而实用的住所的,而且后人能够进入、获取灵感,并在得到启发后着手建造他们自己的房子。要不是他死的早,他肯定会修缮这座房子,继续扩建;不过仔细想想,他短短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件已臻完工的作品,已是相当惊人。不过,这座房子并非角角落落都同样有趣 —— 那不如就把1976年的《撒旦一击》(Satan’s Brew/Satansbraten, 1976) 当作疏通管道,同年的《中国轮盘》(Chinese Roulette/Chinesisches Roulette, 1976)当作埋铺缆线。那三部后来被称作“德意志三部曲”的电影,才是磐石般的基底,是屋子的中央楼梯。大型音像制品商城Zavvi.cn目前举办限时优惠活动Arrow Academy 影碟买 2 送 1!八部法斯宾德影片优惠中 !ThirdWindow Films 影碟 2 张158元满660元免邮 海外货源直送国内更多信息请关注官方微博 @Zavvi官网在评论区留言,谈谈你心中的法斯宾德我们将抽取一位读者,获得 Zavvi 赠送的箭影4K修复版《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跟多数簇立在他周围的房子不同,那些房子以脆弱的现代为基底,无法挖深(怕挖到纳粹的烂根),法斯宾德的房子以历史做基底。“为了能让自己的梦有地可栖,他可真是殚精竭力。”法国评论家赛尔日·达内(Serge Daney)在一篇刊登在《自由报》(Libération )上对1982年上映的《维洛妮卡佛丝》(Veronika Voss, 1982)的评论中写道。“但作为导演,法斯宾德的任务是从零开始,一个个重现所有真实的事物,这些事物必须绝对真实,否则这梦便无法转世重生,也就与一出仿古虚构戏没差别了。”《维洛妮卡佛丝》剧照法斯宾德知道作为一个活在七零年代的德国人,必须完成一些真真正正的类似历史学的工作:要重现的并不仅仅是过去的图像,而是过去的思维方式,光承认历史的失忆症还不够,你还需要尽力去理解这失忆症是如何呈现,以及为何呈现。“当我看到德国人对于‘犹太大屠杀’如此大惊小怪,”法斯宾德曾就德国人对一档主题为大屠杀的美国迷你电视剧集表现出的惊惶反应做出如此评论,“我不知道他/她们为什么如此大惊小怪;她/他们难道真的将这些历史全都深埋,就此忘怀了吗?这不可能的;当他/她们在建造新国家的时候,这些人和事一定在他/她们的脑中盘旋。如果这么重要的一件事都能被压抑、被忘记,那么这个民主制度和这个‘德国模板’一定大有问题。”他知道所有的路都指回那个灰色的、道德缺失的50年代,以及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所发生的年份。法斯宾德知道他必须手脚麻利才要让他的房子有价值,意思是他做到了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他的行动同他的感情和思想同步。他想要,也做到了将生活这一动作本身和故事片拍摄直接绑在一起。这在拍电影这一行里几乎不可能做到,因为遥遥无期的等待会让你举步维艰,一切都是那么费劲,缺钱,缺人,战术上和战略上的难题,忍耐力测试,以及为了拍到一个拿得出手的画面所需要付出心血。也难怪他需要诉诸可卡因和各式各样的其它毒品。老实说,他要不那么做的话,才让人吃惊。法斯宾德遵从“一刻不停”的工作信条,这让他不受限于某种特定的“上帝视角”,这种视角在现代电影中屡见不鲜。法斯宾德总是和他的角色们共进退,同时、同步、想其所想。“你要干坐着等到一件事情变成一个传统吗?”他曾说,“难道你不该卷起袖子,试着建立一些个什么吗?”如果你长时间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你就会想给所有事情盖棺定论;这让你产生一种错觉,自信到以为自己在给人间下最后的定论。通过建造自己的房子,法斯宾德其实是在创造一整套全新的德国电影,这套新电影在政治观念和精神思想上和那些虚伪矫饰和冷漠无感的先人和来者争锋相对。他试图仅凭速度与决心绕开那些晦涩笼统的总体性和夸夸其谈的公式。“法斯宾德的电影总让人感到一切正在进行中,看他的电影你能感受到这部电影被拍摄时的状态,”评论家曼尼·法博如是说。那种现在进行时的感觉,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幕后那个同步思考,同时反应的人,一直持续到最后。即使是他后期那些更加炫目,声势更大的影片,如《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 1980),《绝望》(Despair/Despair—Eine Reise ins Licht, 1977),也同样如此。《亚历山大广场》剧照法斯宾德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力。崇拜他的人照着他的样子,将道德从他/她们的叙事基底中去掉。但很少有人成功(我想到的成功例子有奥利维亚·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和安德烈·塔西尼(André Téchiné)),因为她/他们都缺少法斯宾德所有的一双无尽的、温柔的眼睛:即使他的主角们表现出再多不适,抱怨不休,这双温柔的眼睛都能让人释怀。他目光充盈,定定看着那些从默片时代结束后就无人问津的人们。“如果有人坐在一张法斯宾德电影里的沙发上,我会觉得好久没见过电影里的人那样坐在一张沙发上,至少对我来说,是很久很久没见过了,”法博(Farber)在1977年的一次访谈中说到。“这是一个坐在小沙发上感到不适的大个子 。一个女人站在一道法斯宾德电影的门框里 ——这画面真太美了。他的电影总有一种残暴的感觉,总有人感到不安,产生厌恶之情。迷狂的灯光之下,好比安杰利科修士和僧侣体。”法斯宾德影像的可塑性几乎无人可及 ——就有声电影来说,只有卡尔·西奥多·德莱叶(Carl Theodor Dreyer),小津,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和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在各自的巅峰时期创造出相似的美和力度。但法斯宾德作为创造者还有所不同。他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这个视角抽空多愁善感的情绪,甚至剥离优雅,但仍旧充满同情。在法斯宾德的电影里,我们能看到一个充满人性奇迹的神奇世界向我们展开,这个世界被包装成童话故事,而这个童话故事里到处是绝望、背叛、阴谋、伪善和无知;在这个故事里欲望是个大配角,令人悲伤的是,权力意志是绝对的主导。和一些人的看法相反——而我向来坚持这一看法——法斯宾德拍的不是残酷物语之类的电影。那些单刀直入的故事,其实迫切地想要为世上像玛丽亚·布劳恩(Maria Braun ),维洛妮卡·佛丝(Veronika Vosse)和罗拉(Lola)那样的女人们发声。一方面,这些电影像钝掉的乐器,但更重要的是它给了这些凡夫俗子所应得的照顾和关注。法斯宾德将他的角色们保护起来,免受理想化和多愁善感之类的疾病感染。对他来说,没有超然空间:没有对岸,也没有任何终极现实。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赋予了无比张力的、升华的、富饶的人性。在他的电影里,没一个人活得优雅从容,但每个人都变得如此高贵。法斯宾德*****“我们可以把有关女人的故事讲的更好,“法斯宾德在一次提及德意志三部曲时说道,三部曲由他和作家彼得·马特斯海默尔(Peter M?rthesheimer)和皮·佛罗里希合编(Pea Fr?hlich)。“男人总是按社会期望行事。”“Wirtschaftswunder”,也就是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究竟如何发生?认同自由经济的人觉得这得归功于战后德国联邦经济部部长的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948年六月,在全国道德和经济状况双双陷入谷底的关头,艾哈德向全国人民广播了两条重要决定:德意志马克将取代当时已经一文不值的帝国马克作为通用货币,并且每个公民允许以1:1的比例用帝国马克兑换40个新的德意志马克。艾哈德还史无前例地借鉴了纳粹时期的举措:降薪同时控制物价,先是在控制消费品物价,六个月后食物也是一样,这是连盟军都没有料到的一招。当然,很有可能的情况其实是不管当时政府实行什么政策方针,德国的经济总归是要反弹的,毕竟身处谷底的德国已无法再往更低处走,只有走高。换句话说,这一时期是重建国家的热潮期。法斯宾德对于奇迹发生的原因毫无兴趣,他更想探讨的是一个不怎么时兴的话题,即“奇迹叙事‘究竟是如何成形的,而人们到底要多健忘才能让这一“奇迹”继续存在下去。三部曲里的每一部(“三部曲”正式成为“三部曲”,是在1981年《罗拉》(Lola)的片头中出现”BRD3”时)背后都有一个流产的项目。《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 》(The Marriage of Maria Braun/Die Ehe der Maria Braun ,1979)一开始其实是法斯宾德构想的一部分集电影,计划由爱德嘉·莱兹(Edgar Reitz),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ndorff),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分别执导,取名叫做《我们父母的婚姻》(The Marriages of Our Parents/Die Ehen unserer Eltern)。法斯宾德早就开始构想玛丽亚·布劳恩的故事,不过当时他正扑在另一个大项目的改编工作上,即《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因此他去找了电视制作人马特斯海默尔(M?rthesheimer)和他的搭档弗洛里希(Fr?hlich)。《亚历山大广场》剧照罗密·施奈德(Romy Schneider)本是饰演玛丽亚·布劳恩(Maria Braun)的原定女主角,但据罗布特·卡茨(Robert Katz)的那本无比骇人的法斯宾德自传《爱比死更冷》(Love Is Colder Than Death)——这本书里充斥着一群怨妇情人和陈芝麻烂谷子的花边小料 —— 提到,当法斯宾德将施耐德称作一头“蠢牛”时,这事儿就黄了。法斯宾德决定启用之前合作过《寂寞芳心》(Effi Briest/Fontane Effi Briest, 1974)的女星汉娜·许古拉(Hanna Schygulla) 主演女主。法斯宾德最卖座的一部电影,也是许拉古最棒的一次银幕表演于1978年一月至三月间在科堡和柏林拍摄;法斯宾德在同一时期创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如果你对他当时嗑了什么药,在科堡的旅馆住宿环境有多糟,或是他如何暴虐剧组的演职人员感兴趣的话,去读一读卡茨耸人听闻的传记就好。不过,这部才思敏捷,创意惊人的影片足以证明了他的控制力,眼界和自律——更不用说他的天才了。带着《绝望》(Despair,1978),法斯宾德挤进了当年五月的戛纳影展,《绝望》改编自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英文原版小说(由德克·博加德(Dirk Bogarde)主演,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担任担任编剧)。但真正引起轰动的是却是在一场私人放映上的《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的一盘拷贝。从世界各地来的买家们全都抢着要得到这部电影的放映权。现如今的人们保守,正襟危坐在大剧场,各种状况无限复杂,简直难以想象《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这样的硬骨头在当年居然能大获成功——即使片中时不时会有许拉古衣不蔽体的美妙场景。《罗拉》表面上是三部曲的终章,但按照时间排序上来说其实是第二部,当时德克·博加德(Dirk Bogarde)想要和导演合作另一部混乱又好看的影片,所以这部电影就被忽略了。他的想法是拍摄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一书;约瑟夫·冯·斯登堡的《蓝天使》(The Blue Angel/Der Blaue Engel, 1930)也是改编自该书。《罗拉》剧照法斯宾德的制片人谨慎地从亨利希·曼那里购买了版权(估计是想顺便把《蓝天使》的翻拍权也买下来)。马特斯海默尔和弗洛里希将作家笔下的英雄全盘推翻,让电影中的主角博姆,一个包工头,自取其辱;先是让他在公众面前撒泼,表明对于无良皮条客和大亨舒克特的痛恨,接着让他陷入一种对于往昔的乡愁,否认现实。法斯宾德和他的摄影师克萨韦·施瓦岑贝格尔(Xaver Schwarzenberger)看了很多50年代的彩片做参考——如果说《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中的色彩黑暗而充满阴影(像是染上耀目色彩的40年代末的华纳黑帮片),那么《罗拉》(Lola)则充溢着挑衅的亮色,热粉和血红夹杂着浅绿和淡蓝,一股扑面而来的冲动和肉欲。前东德影星阿明·缪勒-斯塔尔(Armin Mueller-Stahl)申称他和一众演员们随时准备进入“红灯区”,以光速完成表演拍摄。这些都发生在1981年。《维洛妮卡佛丝》(三部曲之二)是法斯宾德生前拍摄的倒数第二部影片。这部电影基于陨落的德国影星西比·施米茨(Sybille Schmitz)的真人悲剧。施米茨在纳粹掌权期间继续拍摄电影,她最为美国观众熟悉的是在德莱叶的电影《吸血鬼》(Vampyr,1932)中的表演。据米歇尔·图特贝格(Michael T?teberg)说,年轻的法斯宾德在报上读到施米茨1955年在慕尼黑自杀,以及随后轰动一时的审理报道,他就和编剧一起将主角姓名改掉,然后借用了一个好莱坞经典套路——一个记者对一个故事着了迷,并将自己的整个人生都贴了进去——想想1941年的《公民凯恩》。法斯宾德决定在1981年末开机拍摄《维洛妮卡佛丝》(The Longing of Veronika Voss /Die Sehnsucht der Veronika Voss),此前他正在筹备《可卡因》(Kokain),这个项目更加复杂难做。《维洛妮卡佛丝》作为一个过渡项目开机,迷倒众生的罗泽尔·泽希(Rosel Zech)二度出演法斯宾德的电影。德意志三部曲之二将成为法斯宾德继《寂寞芳心》( Effi Briest)之后再次尝试黑白电影。这部电影也将是他最后的杰作,他的终章,在历史、政治和美学上都站得稳脚跟的佳作。《维洛妮卡佛丝》剧照*****法斯宾德到底想用这三部相似却不同的电影讲一个怎样的故事?单从时间顺序来说,他其实是在记录一个逐渐解体的过程,在更新、换代、向前进的掩盖下,他要说的是从失忆到含糊再到压抑的过程。我们从战后的行动开始(玛利亚·布劳恩决定去做妓女——从生意到生意人——再到一个崇高的结局),继续发展到50年代中期(维洛妮卡的医生抹去的不仅仅是一个纳粹时代的影星,更多的抹去借由她所代表的一个时代),最后则是50年代后期将一切合理化的思想(博姆和罗拉结婚,随后便退回到一个想象中的的前纳粹时期的安全区中,因此她的皮条客和金主舒克特才能够安心无忧,忽略每一个显而易见的暗示。)法斯宾德同时也在讲述有关这三个虚构的女主角的个人故事。玛利亚·布劳恩和罗拉不得不表现倔强,为了从零开始创造自己的未来每日一刻地不停工作;她们以性作为武器,至少是交换的工具。格格不入的则是维洛妮卡佛丝,被诅咒、被唾骂,一个陨落的巨星,一个卡茨医生觉得可以随心所欲不受罚去敲诈恐吓的女人。如果玛利亚·布劳恩和罗拉是被环境所迫而不得不将自己放低至这些卑微而又矛盾目标,维洛妮卡则是一具残骸,象征着无人问津的过去。跟玛利亚和罗拉不同,她被恐惧和困惑所累,整个无法动弹,仅靠乞求一点人们对于她过去辉煌的认同过活——这一切都和她的人性相通。这三部电影的气质由三位非典型女主角色定调。许拉古饰演的玛利亚·布劳恩不仅慵懒,迷人,而且人戏合一。尽管一直被拿去和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比,许拉古却从来不夺目,她更多地让人感觉到炽热。硬要比的话,她更接地气,婴儿肥和无精打采的眼睛诉说着惯常日子的单调无聊。她出演的所有电影总有一种催眠般的调子,而她所饰演的玛利亚是一个绝佳的祭品,一个用绝望的慢动作试图逆转历史的非凡的工作机器。与此相反,《罗拉》里的巴巴拉·苏科瓦所饰演的妓院里的明星则像飓风,行动、说笑、风驰电掣,完美地和青少年期的坏脾气和被伤害的自尊所调和。阿明·缪勒-斯塔尔饰演博姆,马里奥·阿多夫(Mario Adorf) (凭施隆多夫《铁皮鼓》[The Tin Drum/Die Blechtrommel, 1979]中的父亲一角为美国观众所熟知)饰演舒克特,两人在戏中做了极好的陪衬。《罗拉》剧照不同于以往的一系列法斯宾德电影,这套三部曲每一刻都持续不同地加码,最终将电影推至一场混战,一场演技上的奥林匹克比赛,他/她们为这三部电影带来令人窒息的速度感。如果说克劳斯·洛维奇和伊凡·德斯尼不过(不多也不少)是让许拉谷可以懒洋洋地时而围着他们转,时而跳开的冷漠的男性角色,那么西尔马·塔特( Hilmar Thate)饰演的要将一切刨根问底的体育记者则是和维洛妮卡一起历经了相同的黑暗时刻(很难说他为什么要追寻维洛妮卡的神秘生活,并在此过程中放弃了自己默认的女友——在这个行动的展开中,他看起来似乎是选择了一条更为迷人的死胡同)。泽希饰演的维洛妮卡和想象中性感的女郎毫不搭边,而是一只在强光中颤抖的小鹿。当你对许拉姑和苏科瓦那曼妙的身体念念不忘时(她们两位通常身裹黑色贴身内衣),泽希那死亡假面般的面孔和生猛的感情却缠着你不放。这绝不是说她没有演技。泽希饰演的维洛妮卡十分复杂,她是真实生活这出恐怖电影里不幸的女主角。法斯宾德是个非凡的易容大师,在每个项目中更改调度,调性和节奏,德意志三部曲也不列外。《玛丽亚·布劳恩》是在紧巴巴的预算中拍出来的有关人生起伏的史诗,它那由女人自己选择以导致自身结局的女性叙事借自《欲海情魔》(Mildred Pierce,1945)一类的片子。电影的调子十分尖锐,不时地又让人感到沮丧和警觉,节奏则由玛利亚自己的冲动和欲望所推动。《罗拉》又是另一番不同的如观野兽般的体验,这是一个由幻想和投影构建的一场向兴高采烈的舒克特和正襟危坐的博姆发起的战争,其中罗拉将自己用来打破权力。这可能是法斯宾德后期电影中最富动感的电影——奔放明亮的蜡笔一样的光影,摄影机的移动一刻不停,让人感到喘不上气,有如电扇从空气中聚集废料般地收集尖利和生动的细节。《维洛妮卡佛丝》又与前两部有所不同,这部伪装成《公民凯恩》实则给人带来嗑药一般沉浸之感的电影,在调子上很像法斯宾德早期的电影《十三个月亮》(In einem Jahr mit 13 Monden, 1978),罗伯特对于调查的叙事从来都未成势,但那种深入骨髓的焦虑感却在每个场景中无限延伸。在这样一个极度敏感亢奋,过分拥挤的世界里每一帧都刺得人生疼,这部黑白电影以最大的穿透力捕捉到了这个蔽塞的内部世界,更像是一次X光,而非致敬好莱坞。法斯宾德是节奏天才,他的每部电影里都能带来充满力度和重量的布景。电影中有非常棒的小范围时间,好比玛利亚的情人和刚回家的赫尔曼在一个小黑卧室里,罗拉和博姆在一间乡村教堂奏出甜美和谐的乐章,又或者是维洛妮卡在电影中段在一个电影片场突然崩溃(片中片的导演原型是马克斯·奥菲尔斯(Max Ophüls)——他正努力想要拍个好看的推轨镜头)。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出音乐剧。70年代所有电影中最美好的场景之一是玛利亚穿着她最美的裙子慢慢走近美国大兵的餐厅。“你愿意和我调支舞吗,比尔先生?我的男人死了,”玛利亚用英语问出这句话的同时,格兰·米勒(Glenn Miller)的“月光小夜曲”(Moonlight Serenade)的头几个和弦响起,而玛利亚和比尔(乔治·博得[George Byrd]饰演)跳起了一支慢舞。《罗拉》中让人屏息的时刻是在博姆意识到他本该贞洁的爱人竟然是当地妓院里最令人垂涎的货色,苏科瓦在在演绎她的夜行版“库普里的渔人”(The Fishermen of Capri)时明显地卯足了劲,充满了狂欢野性和蓬勃的能量。维洛妮卡的“高潮”出现在她的告别派对上,法斯宾德将其与水晶碎片交叉剪辑在一起,以她葬礼上的演出——迪安·马丁的“记忆由此组成”(Memories Are Made of This)作为结尾。《罗拉》剧照这是一个知道如何让他的结尾产生大爆炸效果的导演。法斯宾德并不怎么修改剧本,但他总是会调整每一个故事的结局,尽量节制。博姆带着女儿回到他“开苞”罗拉的田园牧歌天堂,女儿却不自觉地重演了母亲在干草棚里的挑衅姿势,未来似乎已经可以预见。维洛妮卡死在了一间被反锁的屋子里,再一次被强尼·霍顿 “新奥尔良的战争”(The Battle of New Orleans)所折磨,之后罗伯特乘坐一辆阴暗的出租车回到了1860年的慕尼黑体育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结尾要数玛利亚·布劳恩在她豪华的新房里,围着她那沉默不语,纹丝不动的丈夫又蹦又跳,录音机里是赫伯特·季默曼(Herbert Zimmermann)正在热烈地点评1953年的世界杯:一个燃气灶,一只点燃的香烟,连同一次再爆炸,一切都像是一个未来预言,暗示着某种毁灭性的错觉。玛利亚·布莱恩,维洛妮卡佛丝,罗拉,罗伯特,博姆,舒克特,赫尔曼……这些角色既真实可信又像是警世预言,她们都在这卑劣的战后德国中摸爬滚打,试图找到出路。法斯宾德用生命中最后的能量带回了这些失落的灰色年代,或许是因为在这些时刻我们才能最清楚无误地看到人性最脆弱的时刻吧。法斯宾德
-FIN-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贝托鲁奇和戈达尔,谁的政治性更能改变世界?日本第一天团女星,差点被游乐园要了命逃离了审查,中国导演就能拍出好电影吗?与鬼怪和少女悠游,他是日本传奇的映画魔术师100年前的权力游戏!这部9.5分神剧讲述一个国家的灭亡15分钟故事拍出4小时,却成为影史最伟大电影她是好莱坞百变女王,雌雄莫辨的异星生物请为深焦口碑榜投票